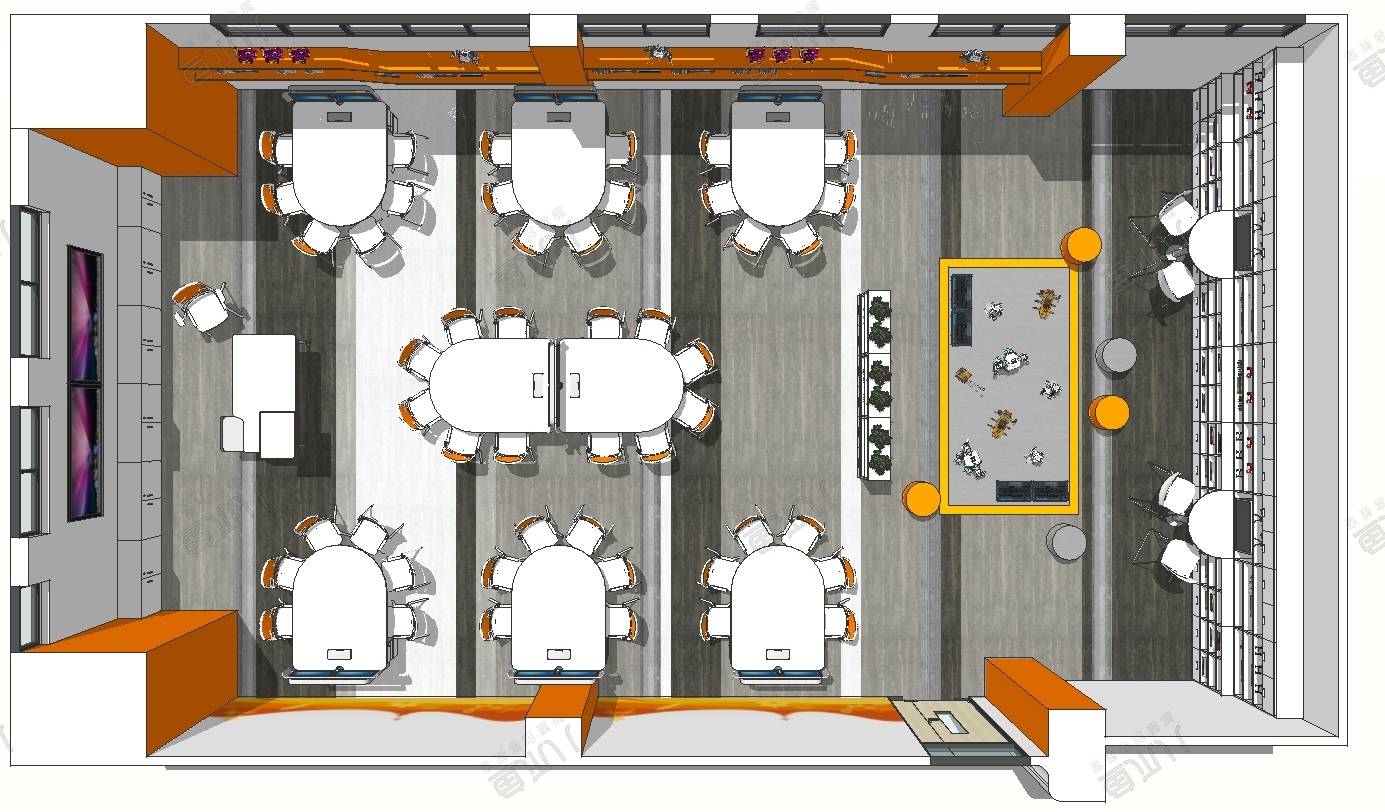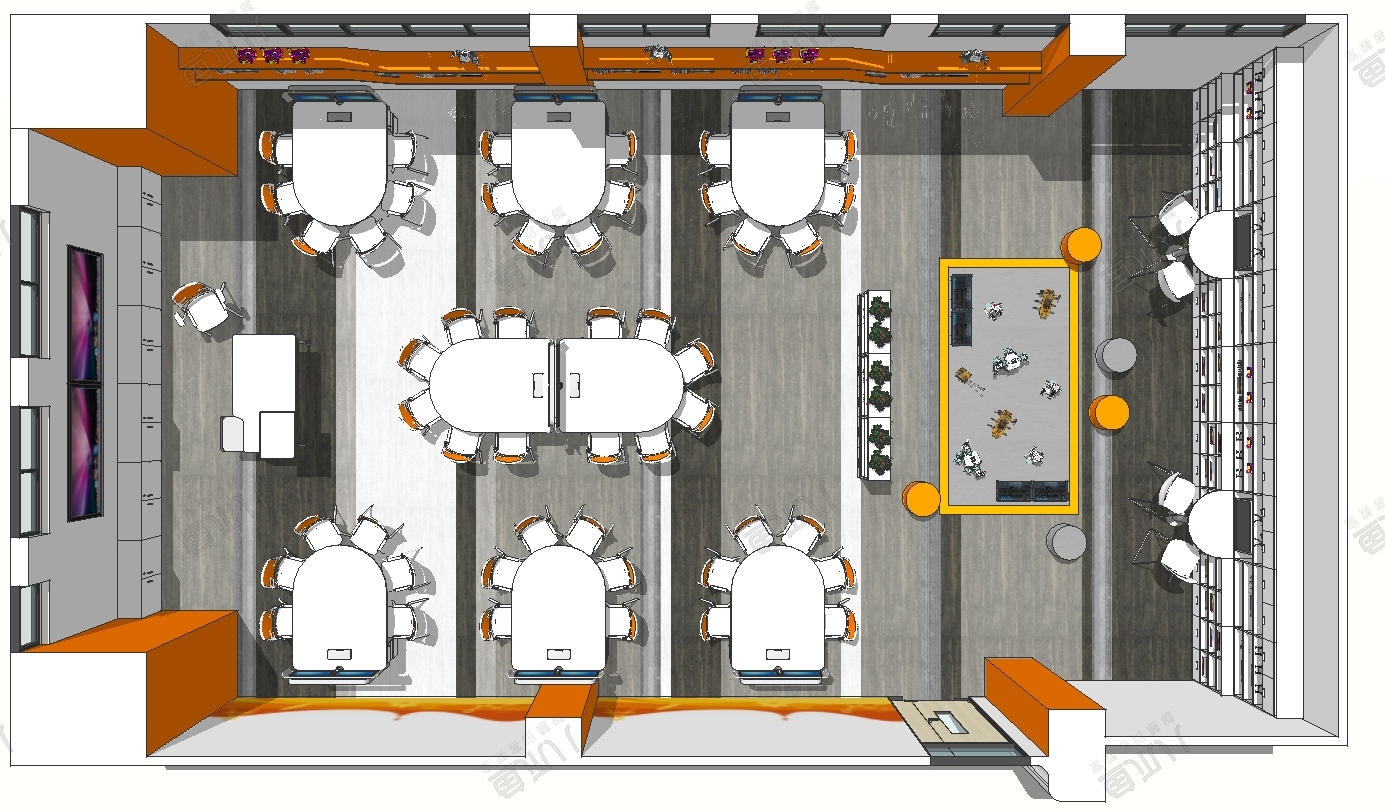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的大学教育充实:自主性和/或文化再
2024-09-12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经济、军事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的根本宗旨和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再次受到质疑(Collet-Sab 和 Ball引用2024;德利索沃伊引用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经济、军事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的根本宗旨和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再次受到质疑(Collet-Sabé 和 Ball引用2024;德利索沃伊引用202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用2021 年)。虽然教育空间通常是根据其正式使命、学生和资格来定义的,但它们的社会角色不可避免地更加复杂和有争议:尤其是在英格兰,中等和高等教育主流之外的学院形成了各种阶级和性别机构,其中结构和机构仍然很重要(Avis 和 Atkins引用2017;科利引用2006 年)。这个多元化的行业经历了政策要求和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最大的群体——英格兰的普通继续教育 (GFE) 学院,在话语上处于英国保守党政府战略规划和脱欧后雄心的核心地位(英国政府(引用2017 年);英国财政部引用2021 年),尽管命运多舛的新“T 级”资格吸引了 10 亿英镑的发展资金(英国下议院),但该行业的资金下降速度快于其他教育领域引用2023;西比埃塔和塔希尔引用2021 年)。学院广泛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可能会与商业和采掘利益纠缠在一起,从而促进职业道路的社会分层作用(Esmond 和 Atkins引用2022 年;麦格拉斯和鲁森引用2023;王和王引用2023;Wheelahan 和 Moodie引用2017 年)。


在本文中,我们在“充实”的背景下研究了英格兰学院的社会角色,“充实”曾经是一个看似边缘的非资格规定领域,在英国政府技术教育政策的“回归学科”期间成为强制性规定,并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时变得越来越突出(Avis 等人。引用2021;教育部/DBEIS引用2016;年轻引用2011 年)。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环境中,提供考试科目教学之外的松散定义的实践成为公共资金的要求,并受学校和学院督察机构的判断(ESFA引用2022);英国教育标准局引用2022 年)。这里回顾的这项为期四年的研究首先追踪了它在年轻人进入工作和成年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普通继续教育 (GFE) 学院,工人阶级和弱势学习者占比过高,这种非资格规定传统上一直试图弥补优势家庭的孩子部署和积累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形式的机会(Atkins 等人。引用2023 年;Lareau 和 Weininger引用2003 年;雷伊引用2000 年)。该研究后来具有进一步的意义,因为它是一项纵向研究,研究了大学对疫情后混乱和危机的变化反应,提出了扩大大学与学生和社区接触的可能性;然而,在 16 岁以后教育的等级制度中,这种资源不足的活动有可能成为新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地。
一个核心难题,也是本文的理论重点,是教育机构和教育途径在社会中的不同定位、它们的文化期望以及它们允许的自主程度。一个长期存在的范式认为,学院中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主要促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Esmond 和 Wedekind引用2023年;格里森和马德尔引用1980 年;西蒙斯引用2010 年)。虽然早期的理论被广泛否定,认为其是决定论,而不是中断繁殖的可能性(例如苹果引用1982 年;艾维斯引用1994;汤普森引用2019),后一种可能性几乎总是与技术领域脱节:在继续教育中,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与技术课程一起教授的通识教育,几十年后仍然是一个著名的事件(Huddlestone 和 Unwin引用2024;帕特尔引用2024;西蒙斯引用2016 年)。在有关资格、流动性和抱负的政策辩论与全球南北地区不平等加剧及其持续存在的严峻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这些讨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米兰达和阿尔弗雷多引用2022;塞拉和盖尔引用2011 年)。在健康、经济和环境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文化和物质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新的生育理论已将其范围扩大到教育领域(例如亚伯拉罕引用2024;雷伊引用2022 年),并超越了生产界限,进入了家庭领域(例如 Backer 和 Cairns引用2021;巴塔查里亚引用2017 年)。在此,我们借鉴了这些论述以及我们自己对普通路线与职业路线之间以及技术/职业路径内部不断加深的分层的分析(Esmond 和 Atkins引用2020年,引用2022),以检验大学社会角色的这种典型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以丰富和超越社会。
我们的实证研究涵盖了整个 16 岁以后的大学领域:GFE 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 GFE 大学和六年制大学 (SFC) 中以通识教育和学术进步为中心的通识教育途径,从而能够跨机构类型和教育空间比较一系列目标、活动和为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的代理。这些方法展示了不同教育空间中(重新)产生的社会关系,使我们能够反映英国大学及其当前和潜在的社会角色。在以下章节中,我们首先讨论充实对于研究大学社会角色的重要性,阐述这一系列机构的范围,然后转向对大学与结构、代理和分层关系的理论理解,在大学部门和更广泛的社会发展中定位非技术环境中的“抵抗”描述。然后,我们描述了我们的实证研究方法及其在四年的调查、访谈和案例研究中的变化形式。我们报告的研究结果说明了在不同环境下塑造丰富内容的独特实践,指出了与英格兰 16 岁后教育结构的联系以及这些结构赋予的代理可能性,以及它们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这反过来使我们质疑如何设想更加社会公正的 16 岁后教育安排。
在不断变化的大学使命中定位非考试课程
评估科目教学以外的活动在整个中学教育中发挥了多种作用,有时包括在大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和投入。与主流课程一样,这些发展反映了它们在教育政策及其他方面不断变化和有争议的优先事项中的位置(Bathmaker引用2013年;霍奇森和斯波尔斯引用2008年,引用2019 年)。在大多数英语国家,学院都是多元化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在英格兰,158 所 GFE 学院提供最多的职业教育,而 44 所六年制学院 (SFC) 更侧重于大学升学;英格兰共有 225 所学院,由专科和陆基院校组成,而威尔士的 13 所学院中有 12 所被归类为继续教育学院;混合空间包括 GFE 学院内的“六年制中心”(学院协会引用2024)。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追踪这些机构类型中的丰富性及其独特的作用并探索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式置于更广泛的经济和教育历史模式中:英国战后的技术学院主要教授15岁就辍学的兼职日间放学的年轻工人,由于担心他们的读写能力、算术能力和人文价值观,无法理解实用技术课程的意义,国家出台了政策干预措施,要求引入地方组织的自由研究、综合研究或社会研究课程(Bailey and Unwin)引用2008年教育部引用1959年,引用1961 年)。这些课程涉及艺术、电影研究或政治教育等领域,通常由当时大学技术核心以外的教育工作者主持(Ecclestone引用2002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该期刊的 39 篇论文反映了教师的热情以及学徒的褒贬不一的反应,编辑们将这些论文归类为“文科”和“社会研究”(数量是技能教学和“工业培训”的两倍)(《教育的职业方面》编辑引用1969 年)。这些安排反映了战后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相对平静的社会,尤其是国有企业培训了大量学徒(Fuller 和 Unwin引用2009 ). Bailey 和 Unwin (引用2008 年)认为,该项规定的废除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将其纳入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的技术资格要求有关,但 Haselgrave 报告(DES)引用1969 年),这导致了这些发展(后来的 BTEC 资格,现在被归类为“应用通识教育”),主张以“最适合当地需求和情况的方式”继续进行通识教育或文科教育(DES引用1973,84)。这一判断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技术教育学院的相对自主性和地方重点,以及它们相对较低的地位(Simmons引用2010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兴起,自由研究最终被淘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培训的外部发展。与此同时,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采用最小化和市场化的“学徒制”(Ryan 和 Unwin引用2001 年以来,一种表演文化开始渗透到继续教育学院,并由“提供者”和“交付”等新术语、辅助专业人员的雇用以及通用“技能”教学以及读写和算术方面的“功能技能”教学所支撑(Brockmann 等人。引用2008;埃斯蒙德引用2020 年;格里森和詹姆斯引用2007 年)。这一时期,狭隘的能力评估和国家职业资格 (NVQ) 取得了胜利,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基于能力的培训 (CBT),它们在文化上主导着学院,其“任务分散、定义狭窄,基础知识极少”(Brockmann 等人)。引用2008,227)供给侧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表达(霍奇引用2016 年;穆迪和惠拉汉引用2023 年)。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对于大多数职业学生来说,通识教育的残存要么被主流课程所掩盖,要么被孤立在补习活动中,尤其是针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正如 FEU 所记录的那样(引用1985 年,FEFC(引用1996 年)列出:
…体育、音乐、戏剧、文化和实践活动、工作经验和工作见习、住宅访问和学习旅行、对外交流、健康教育、个人和社会教育、宗教教育、语言、信息技术、小组项目、户外活动、俱乐部和社团以及休闲兴趣。(FEFC引用1996年,2)
这份广泛的清单代表了一系列可能性,而不是学习者在继续教育课程中的常规经历。尽管如此,它既表明了对此类经历的重视,也表明了扩大教育范围的相互冲突的野心,同时在前者成为沃尔夫 (引用2011 年)。这项规定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继续吸引资金,因为它与通用课程和成绩较差的学生有关(Atkins 等人。引用2023 ). Ofsted (引用2014 年)对充实活动进行了积极但有些零散的概述,其中交织着工作经验的描述,并报道了当地威胁要撤回普遍提供以管理资金削减的情况(Ofsted)引用2014,17)。
近年来,充实教育的重要性与 2010 年以来学校课程转向“知识型”课程相伴而生。英国政府的“技术教育”改革旨在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途径,旨在取代与一般进步主义相关的低级资格证书和成为进入低级大学课程的途径的“应用通识教育”(Esmond引用2018 年;特里和奥尔引用2024;杨与甘布尔引用2006 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变化具有课程层面,反映了人们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知识、认证和成果获取不平等的担忧(Pring引用1995 年;惠拉汉引用2007年,引用2015 年)。然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充实,我们的关注点仅与资格和课程间接相关:我们的兴趣在于这些学院内的不同机构类型和空间如何实现不同的实践和结果。在下一节中,我们阐述了此分析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文化再生产与教育空间
一支长期致力于社会公正的团队(Atkins引用2009;Atkins 和 Duckworth引用2019;埃斯蒙德和阿特金斯引用2020年,引用2022;考尔引用2023年,引用2023b;罗尔斯引用1971 年;森引用2009),反映了人们对“可以用来吸引最边缘化学生的教学方法”的兴趣(Atkins 等人。引用2023 , 97)。除了与学科相关的象征性控制之外,充实还被视为“文化知识的潜在空间……对学生及其家庭很有价值,但……在学校环境中不一定被认为具有任何资本”(Yosso引用2005,76)。虽然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可能最常在课程内容方面被讨论,但学科课程之外的文化实践的意义可以追溯到杜尔克姆(例如杜尔克姆引用1961年)。
然而,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灌输的文化也可能参与到生育过程中。在早期的法国记载中,格里尼翁(引用1971 年)注意到,技术路线通过围绕阶级身份的(再)生产构建的话语,向“学业不成功”的工人阶级青年灌输一种“技术道德”,强调所有问题都有技术解决方案的存在:格里尼翁认为,这些背景也提到了一种精英文化(“堡垒话语”),以“向学生们表明,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这种精英文化”(迪金森和埃尔本译)引用1982 , 146)。Tanguy (引用1985 年)将法国的学士学位和技术课程(当时的 CEP 和 BEP)的要求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青年的不同文化期望直接联系起来。Tanguy 将学士学位学生的学习时间较短归因于中产阶级青年需要“获得相对活跃和批判的态度”(Tanguy引用1985 年,24),而工人阶级的青年,尽管他们被认为在学术上存在局限性,却需要学习更长时间,以便获得工作纪律和服从的态度。而法国的学士学位则包括技术和职业路线,并有“旨在丰富学习的可选活动”(Martin-van der Haagen 和 Deane引用2003,86),这些文化差异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英格兰。
这类文化问题一直是布迪厄学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学科外的参与教学被认为是赋予和对抗结构性劣势的机制。对于雷伊(引用2004)丰富化被视为“个人遵守(或不遵守)学校教育评估标准的微观互动过程”之一(Reay引用2004,73)。这些分析关注的不仅仅是布迪厄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证书和资格)的获得,还包括文化商品和具体实践,例如在《区别》(布迪厄引用1984;另见布迪厄引用2021,161ff)。这些概念在与中学后教育相关的问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 Bathmaker 及其同事讨论了中产阶级大学入学者的文化优势,后来在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了认可(Bathmaker、Ingram 和 Waller引用2013 年;Ingram 等人。引用2023 年)。将继承的文化属性转化为证书和财务成果的货币,被认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机会产生了有害但经常被否认的影响”(Reay引用2022年,8)。
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反映出这些著作所著国家的教育结构,在教育在再生产社会中的作用的基础性论述中很少直接讨论,教育引导年轻人进入接近其父母的社会空间。布迪厄和帕瑟隆(引用1990 年)泛指“那些最不可能进入下一阶段教育的学科”(Bourdieu 和 Passeron引用1990,153 ),以及 Bowles 和 Gintis (引用2011 年)简要地将社区学院定义为社会化的场所(引用2011 , 205–213)。然而,在英国,这些思想是在当时继续教育学院的特定背景下被采纳的,Gleeson 和 Mardle(引用1980 年)挑战了教育和培训与“人力”需求“同步”的观念,指出其在再生产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这些论述中社会再生产的驱动力不是他们的职业课程和行业技能教学:相反,社会化进入工业生产关系可以引导人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社会关系(见 Avis引用1981年,引用1994 年)。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大幅减少,但这一立场并没有改变,学院从主要为年轻工人提供非全日制课程的机构转变为为失业青年提供普通“职业前”教育的大型机构。摩尔 (引用1987 年)描述了如何“将‘工业需求’的意识形态表述转化为课程形式和相关的教学实践”( Moore引用1987年,230)。
我们的兴趣不仅限于对制度再生产本身的分析,还延伸到在特定环境中中断制度再生产的可能性。注意到那些对学校教育的批判性论述,这些论述将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与职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例如阿罗诺维茨引用2016 年;吉鲁引用2001),我们试图了解结构性劣势/劣势的延续是否以及如何被打断,无论是在大学生活的主流还是在替代实践中。在 16 岁以后的大学中,这种可能性最常出现在技术领域之外,例如在大学通识教育、非技术或成人教育中(例如 Aggleton引用1990 年;艾维斯引用1985 年;Merrill 和 Hyland引用2003 年)。上文所讨论的通识教育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观点,例如,“通识教育旨在缓解异化问题”(尼尔引用1966,3),这些观点通过最近对“批判教育学”的引用得到了延续(西蒙斯引用2016 年)或祈祷,以替代撒切尔政府和新工党政府统治下的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狭隘的、基于能力的方法(哈德尔斯通和昂温引用2024 年)。他们提出了在同一机构内中断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可能性,但在与技术或继续教育学院的核心规定不同的社会逻辑空间中。然而,他们的临时安排、不均衡的后果以及与当时核心技术教学(和教师)的分离,引发了人们对单独提供通识教育要素如何有效地挑战阶级教育不平等的持续存在的质疑。
现在,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视角将这些环境视为争论的空间,社会学对生育的理解延伸到家务劳动、照料和全球化,包括弗雷泽的(引用2017 年)将“照护危机”等同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弗雷泽引用2017 , 22)。这些扩展的生殖视野表明,生殖与从生到死的整个人类生命繁衍实践之间存在着进一步的纠缠 (Bhattacharya引用2017)为不断加深的教育鸿沟提供了背景,Esmond 和 Atkins(引用2022 年)指出,加强与工作场所的接触导致学生的经历和结果出现分层,不仅是在普通途径和职业途径之间,而且在职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我们对“福利职业主义”的识别描述了年轻工人阶级女性被吸引到以护理为基础的和其他被低估的途径,这是性别社会化就业的一部分。相应地,我们讽刺地将那些在男性继续教育中心获得技术工作机会的学生称为“技术精英”,这主要是从这些学生的相对特权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例如 Avis引用2022年,引用2024;Avis 等人引用2021 年)。然而,任何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机会以及进入英国政府“高等技术教育”的途径所带来的好处,都是以文化狭隘为代价的,而文化狭隘是与不太重要的高等学习形式相关的。这些是我们讨论充实的核心问题,下一节将继续讨论我们项目的方法论基础。
纵向研究:方法论
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提供更多关于持续充实实践的知识。虽然 Ofsted 的(引用2022 年)“教育质量”的定义现在开始参考“旨在为所有学习者提供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和文化资本”的课程,但关于其获取的明确信息很少。随着教育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社会正义中心引用2021;Donnelly 等人引用2019;罗宾逊引用2024 年,教育慈善机构 NCFE 委托该研究,并得到了该行业管理机构大学协会 (AoC) 的支持,其广泛目标是“对充实内容进行更多定义和澄清”和“确定有效的机构充实计划的例子”。该项目还试图确定具体成果:“充实内容对各种学习者的积极影响”和“充实活动的潜在经济价值程度”。该研究被设计为一项纵向研究,从一项调查开始,然后进行案例研究,其中将跟踪充实内容对学习者的影响,直至他们从大学转入就业或进一步学习。这项为期四年的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包括收集机构调查数据和案例研究,最初计划以区域为基础,包括文件分析和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级管理人员、教师、专业充实人员和学生的采访。然而,在研究期间同意对这些观点和计划进行一些修改。
总体设计可总结如下。首先,向所有附属于 AoC 的学院发送了一份开场调查,收到了 84 份回复。问题来自文献和之前的 AoC 调查,涵盖了充实活动的目标、组织、范围和管理,有 46 个领域需要回答。为了评估这些回复的重要性,在地区基础上进行了后续访谈,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四次访谈,并额外关注了在调查结果中代表性不足的专业机构和 SFA。这些后续访谈导致在每个地区临时选定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最初计划围绕与教职员工和学生会面的一系列实地考察进行。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其他研究一样,这变得困难,因为在封锁期间,教职员工和学生根本不在大学,大流行期间教育组织的压力为与外来人会面创造了困难的环境;谈判访问变得漫长,面对面的采访也变得困难,因此许多会议和采访都是通过 Microsoft Teams 在线举行的,而不是面对面的。此外,到 2022 年实地考察变得常规化时,我们对充实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某些环境中的学生很容易证明充实的持久好处,但很难将其影响与其他教育成果区分开来;而学习者越来越多地将这些活动描述为具有更大的直接意义,例如支持他们继续学习课程。这些因素,加上在疫情期间与受访者建立长期关系的困难,促使我们与合作伙伴和资助者讨论,修改计划以关注长期影响。随着我们对各种充实活动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也开始明白,案例研究的区域选择不如深入研究特定类型的充实实践重要。因此,我们从研究九个地区案例转变为研究九个已确定的丰富活动类别,以一所大学为例,但每个案例都有补充数据来丰富图景。2023 年 1 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收到了 109 份回复,重点关注了为应对 COVID-19 而对丰富活动所做的改变,以及丰富活动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早期传播期间,即在项目结束之前,我们将早期的发现和分析反馈给了数百名从业者,其中许多人希望在补充访谈中分享自己的经验。
案例研究和补充访谈中使用的方法均经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研究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曾在该委员会工作。他们的设计和行为符合 BERA(引用2018)道德准则,并基于我们对社会公正教育研究的承诺(Atkins 和 Duckworth引用2019 年)。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文献证据、观察和拍摄场景;访谈范围从个人访谈、配对访谈到焦点小组,其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在时间和学生允许的情况下,该研究使用移动访谈,学生将带领研究人员前往活动发生的特定地点:与这些空间和场景进行具体、关系和感官的互动(Kaur引用2023年,引用2023b;奥尼尔引用2017;Springgay 和 Truman引用2018 年)。
生成的数据量和种类需要经过多种分析技术,从详细分析调查数据到寻找总体主题。来自不同收集模式的数据(包括转录访谈、现场笔记和图像)被上传到共享空间,以便团队进行比较和三角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团队成员都沉浸在案例研究数据中(惠灵顿引用2015 , 73),并辅以每周团队会议,回顾其新出现的意义,并对新发现进行“持续比较”模型的主题分析(Corbin 和 Strauss引用2015 年)。在构建我们的丰富类别及其与特定环境关系的核心主题时,我们既关注 Glaser 的(引用1965 年)将这种技术与先前的编码区分开来,理由是研究人员不断地重新设计和重新整合理论概念(Glaser引用1965,437 ) 和 Charmaz (引用2006 年)认为,我们长期参与该领域研究为我们的构建提供了信息。虽然我们的案例研究主要基于对不同实践的观察,但我们对 16 岁后机构特定环境重要性的关注是基于对 16 岁后教育不断发展的现实的批判性理解。我们在下一节中列出了我们的主要发现,然后再讨论它们对下面英国学院的意义。
下一篇:没有了
推荐阅读
后疫情时代的大学教育充实:自主性和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经济、军事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多重危机...
职业教育中的教学因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本研究介绍了职业教育中的教学因果机制 (PCM),以此来分析和改...
Bigme 大我 10.3 彩墨屏 B1051C 智能办公本
绿色事迹轻钢别墅行为轻钢安装式修筑范畴的奇特黑马,依靠着...
紧要从事车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智能模
生意目前厉重盘绕煤炭综采筑设液压支架发展,为煤炭分娩企业供...